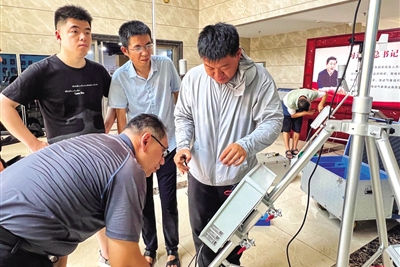谁说石鼓敲不响,激昂的鼓声回响千年
■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张文凯
穿着汉服、摇着团扇,我倚靠在合江亭二楼栏杆旁,向北眺望。
石鼓山犹如一艘破浪前行的航母,毅然插入滚滚洪流。其左侧,蒸水自远方蜿蜒而来,一路奔腾,最终汇入湘江那浩瀚无垠的怀抱。在两水交汇处,它们形成了两股界限分明的水流,却在经历了最初的碰撞与对抗后渐渐融合、共同前行,而两百米开外,耒水自东向西浩荡而来,亦汇入湘江。至此,三支河流汇聚一堂,拉开了向北奔腾、势不可挡的壮阔序幕。
美景在前,自是不容错过,更不容辜负!
东晋文学家庚阐于339年奔赴零陵郡任太守时路过衡阳,他慕名浏览了石鼓山,并将其唤作“灵山”,写下了《观石鼓》。这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首写石鼓山的山水诗。
787年,齐映贬为衡州刺史。虽遭遇不公,但他从未消磨意志。在衡阳五年,他治理有方,深受百姓爱戴,还带头筹集资金,在石鼓山上建起合江亭、武侯祠。
801年,衡州刺史宇文炫在石鼓山东西两侧的崖壁上,刻下了“东岩”与“西溪”二字。历经悠悠1200载春秋,“东岩”已随岁月消逝,而“西溪”二字楷中带隶,规整端正,笔力遒劲,犹如历史之碑铭,令人叹为观止。
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赞誉这里是“一郡佳处”。元代的黄清老评价更高,直接冠以“湖南第一胜地”的名号。
当然,对石鼓山的美,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理解得最深。805年,他路过衡阳时上岛游玩,以《合江亭》为题,二百字一气呵成,挥毫写下了“红亭枕湘江,蒸水会其左;眺临渺空阔,绿净不可唾”的千古名句。至此,合江亭有了雅称“绿净阁”,诸多名人雅士慕名前来,石鼓山成功破圈、声名远扬。


石鼓书院是一本厚重的书
最早一批落户石鼓山的应该是道士。他们在此修建宫观,修行道法。
李宽来了。他是衡阳本地的秀才却淡泊功名,将山上的道院改为书舍,招揽读书人来此清静之地,大家一起读书、做学问,当时的人都称之为“李秀才书院”。
810年春天,吕温被贬为衡州刺史,来到衡阳。吕温与柳宗元、刘禹锡交好,都是唐朝“二王政治集团”的核心人物。颇感怀才不遇、心中抑郁的他,经常会来到石鼓山。夏日的一天,他走进李秀才书院,遇见了李宽(也作李宽中),挥毫写下了《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》,笔端流露出羡慕与期盼。这是有文字记载石鼓书院诞生的准确时间,石鼓书院成为宋初四大书院中创建时间最早的书院。在吕温的扶持下,秀才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。只可惜,他在衡阳只待了一年半,就病逝于任上,年仅39岁。满怀仁爱之心的他恪尽职守、政绩颇著,老百姓尊其为“吕衡州”。后书院毁于唐末的战火中。
李宽的后人李士真,虽一举夺魁中了进士却不愿意入仕为官。997年,他找到当地的郡守,提出个人出资,在旧址上重建书院,以“石鼓”命名。他要承袭祖先遗志,要将书院建成读书做学问、开展学术交流的场所。中国古代书院从唐代开始萌芽,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。从皇帝到官吏,从朝廷到民间,都对培养人才、发展教育表现出深厚的兴趣与责任。
刘沆(995--1060年),曾任北宋宰相、集贤殿大学士。1035年,他来衡阳任知府,非常重视书院教育,于是奏请宋仁宗,请求颁赐院额。仁宗皇帝大笔一挥,又赐匾额又赐学田。此举意味着石鼓书院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。
时间的指针滑到了1185年,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官员和学者潘畤,作为中央派往地方的代表来到衡阳,他倡议对石鼓书院进行了重建。两年后,提刑宋若水拿过接力棒,继续拓展了石鼓书院的办学规模。竣工后,还请当时的儒学大师、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撰文记载此次的重修。朱熹在《石鼓书院记》中阐述了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,提出了“明道义正人心”的教育目的,不仅是对石鼓书院,更是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这篇《石鼓书院记》在2006年石鼓书院重修之际,被镌刻在石鼓广场那本石书上,象征其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和不朽的文化价值。

自由、开放与包容的圣地
仁宗赐匾、朱熹写记,石鼓书院在宋代众多书院中脱颖而出,响彻江南!
不同于官学的教条主义,石鼓书院一直有着开放、包容、自由的学术氛围,并且在宋明时期形成两次影响全国的学术发展高峰期。
南宋长期偏居江南,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郁结,一些人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儒学来提振人心、改变现状。当时,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湖湘学派的张栻、闽学派的朱熹、婺学派的吕祖谦,同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张栻出身高富帅,是当朝宰相之子,虽祖籍四川,但一直随父亲生活在湖南,后又赴南岳衡山拜胡宏为师。他曾多次到石鼓书院讲学,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宝和碑刻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为武侯祠所作的《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》。在这篇碑记中,他颂扬了诸葛亮的忠义精神,也借诸葛亮的事迹阐明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理学思想。石鼓书院成为张栻传播湖湘学派思想的阵地。也正是在张栻的影响下,四方学者接踵而至,石鼓书院成为了南宋理学传播重地和湖湘文化的发源地。
石鼓书院特有的学术氛围吸引了众多志士达人,他们像辛勤的采蜜人一般来到了这里。
湛若水,明朝一位与王阳明并驾齐驱的著名理学家,先后五次踏上这座书院,每一次的到来,都如同春风化雨,滋润着书院内求知的心灵。1556年,那是一个金秋时节,年已九旬的湛若水,不顾年事已高,再次来到石鼓书院,一呆就是60天。也许是最后一节课,当站在书院那熟悉的讲堂之上,他凝望着窗外,心中涌动无限的感慨,于是在讲堂的墙壁上挥毫题下了《石鼓书院讲堂题壁》。在这首诗中,湛若水仿佛与石鼓书院、与流淌的江水、与静默的石鼓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对话。他对石鼓书院的思念,超越了言语,化作了那永恒的笔墨,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邹守益,王阳明门下最得意的弟子之一,昔日以探花及第之姿荣耀入仕,官拜南京国子监祭酒,位尊而权重。然其性情刚正不阿,直言敢谏,终因触怒权贵,被罢官免职。于是,他毅然决然踏上归途,回到故乡,以讲学为业,矢志传承学术薪火。嘉靖中叶,邹守益受王阳明之托来到石鼓书院。他的到来,如同春风吹拂,为这片学林带来了勃勃生机。在讲坛上,他解答疑难,旁征博引,往往能结合身边琐事,辨析入微,深入浅出。他的语言,如同春风化雨,形象生动,听者无不心旷神怡,心悦诚服。邹守益更将这份对学术的挚爱,倾注在与石鼓学子的讨论之中。他将讨论的精髓,悉心整理成《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》,流传后世,成为学术瑰宝。这部作品,不仅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,更见证了他与石鼓书院的不解之缘。
甘泉学派的湛若水与阳明心学的邹守益,两位学术巨匠共聚石鼓,使得石鼓书院成为明朝学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站在合江亭上远眺,滔滔湘水奔流不息。石鼓书院以其广袤无垠的开放胸襟与深邃博大的包容气度,吸引着四方名儒、八方大咖。这里成为了一流学术大师的汇聚之地。他们如同群星璀璨,交相辉映在石鼓的苍穹下,共同织就了一幅绚烂多彩的学术画卷。
石鼓书院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,屹立于历史的风雨之中,博大精深,令人仰止。它不仅仅是一种追求真理、探索未知的执着,更是一种兼容并蓄、和而不同的智慧。这种精神成为了“石鼓著名穹壤”的坚实基石,让石鼓书院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成为了后世学者心中永远的圣地。
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缮,石鼓广场再度对外开放。近日,将儿子从电脑游戏中强行拽出,一家三口驱车来到了石鼓广场。
迎面而来的是一座三门四柱式石雕牌坊,高12.2米,宽19.8米,采用芝麻白花岗岩建造,上书“石鼓江山”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站在牌坊前仰望,泰山压顶的磅礴气势席卷而来,不由心生出敬畏之感。
这里,就是衡阳八景之一“石鼓江山”所在地。
这里的石鼓,曾经被人敲响
石鼓广场的北边就是石鼓山,石鼓山因曾有一面敲得响的“石鼓”而得名。
这并非传说!
郦道元,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,在他的《水经注》里有一段描述:“县有石鼓,高六尺,湘水所径,鼓鸣,则土有兵革之事。”罗含,东晋时期的杰出人物,出生于衡阳郡耒阳县,也是一名地理学家,曾写了一本《湘中记》,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、特产、民俗、古迹。他也证实,确有此事,并且“扣之,声闻数十里”。
每当石鼓发出鸣响时,当地就会有战争或动乱的事情发生。百姓觉得此事不祥,于是有一名叫庐龙的勇士,将石鼓推入了崖下深潭。这件事被记录在了《祥符州县图经》中。为感谢这位勇士,石鼓山上曾经建有庐龙庙,用以祭祀他。
1637年,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来了衡阳,先后两次登上石鼓山。喜欢探究的他想找到那个高六尺的石鼓,却只在合江亭下发现两根镌刻着对联的石柱。
在石鼓山附近的筷子洲上驻扎的湘军也派人潜入深潭寻找石鼓,却只在潭底发现一洞穴,阴森恐怖至极。此后,石鼓的下落,成为不解的谜团。
走进石鼓书院的山门,你可以看到大门右前方有一面石鼓,这是1965年修建石鼓公园时凿刻的,已是一面敲不响的石鼓。尽管如此,它仍然是衡阳人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。你、我,还有他,曾经在年少不更事时爬上那面石鼓,与它亲密合影留恋。今年提质改造后,石鼓广场在南门入口处新添了一面别具新风的石鼓。这面石鼓嵌有电子显示屏,能够展示声音和图像,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与听觉体验。

记者手记
“石鼓江山锦绣华”,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,我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恶补衡阳文史知识。感谢戴述秋、刘洁,他们俩对石鼓书院的执著钻研,为我的采写提供了捷径。我多次独自前往石鼓书院,在石鼓山四处寻觅,努力探究它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火。不管是李宽,还是张栻,亦或是湛若水、邹守益,他们所追求的,无外乎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,也是王船山一直所倡导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
石鼓江山
翠屏突兀俯中流,岳色江声两岸秋。
何处吹箫明月夜,便宜诗酒在南楼。
翠屏突兀俯中流,岳色江声两岸秋。
何处吹箫明月夜,便宜诗酒在南楼。
——明·伍让
《合江亭》问世,石鼓山一鸣惊人
穿着汉服、摇着团扇,我倚靠在合江亭二楼栏杆旁,向北眺望。
石鼓山犹如一艘破浪前行的航母,毅然插入滚滚洪流。其左侧,蒸水自远方蜿蜒而来,一路奔腾,最终汇入湘江那浩瀚无垠的怀抱。在两水交汇处,它们形成了两股界限分明的水流,却在经历了最初的碰撞与对抗后渐渐融合、共同前行,而两百米开外,耒水自东向西浩荡而来,亦汇入湘江。至此,三支河流汇聚一堂,拉开了向北奔腾、势不可挡的壮阔序幕。
美景在前,自是不容错过,更不容辜负!
东晋文学家庚阐于339年奔赴零陵郡任太守时路过衡阳,他慕名浏览了石鼓山,并将其唤作“灵山”,写下了《观石鼓》。这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首写石鼓山的山水诗。
787年,齐映贬为衡州刺史。虽遭遇不公,但他从未消磨意志。在衡阳五年,他治理有方,深受百姓爱戴,还带头筹集资金,在石鼓山上建起合江亭、武侯祠。
801年,衡州刺史宇文炫在石鼓山东西两侧的崖壁上,刻下了“东岩”与“西溪”二字。历经悠悠1200载春秋,“东岩”已随岁月消逝,而“西溪”二字楷中带隶,规整端正,笔力遒劲,犹如历史之碑铭,令人叹为观止。
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赞誉这里是“一郡佳处”。元代的黄清老评价更高,直接冠以“湖南第一胜地”的名号。
当然,对石鼓山的美,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理解得最深。805年,他路过衡阳时上岛游玩,以《合江亭》为题,二百字一气呵成,挥毫写下了“红亭枕湘江,蒸水会其左;眺临渺空阔,绿净不可唾”的千古名句。至此,合江亭有了雅称“绿净阁”,诸多名人雅士慕名前来,石鼓山成功破圈、声名远扬。


石鼓书院是一本厚重的书
最早一批落户石鼓山的应该是道士。他们在此修建宫观,修行道法。
李宽来了。他是衡阳本地的秀才却淡泊功名,将山上的道院改为书舍,招揽读书人来此清静之地,大家一起读书、做学问,当时的人都称之为“李秀才书院”。
810年春天,吕温被贬为衡州刺史,来到衡阳。吕温与柳宗元、刘禹锡交好,都是唐朝“二王政治集团”的核心人物。颇感怀才不遇、心中抑郁的他,经常会来到石鼓山。夏日的一天,他走进李秀才书院,遇见了李宽(也作李宽中),挥毫写下了《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》,笔端流露出羡慕与期盼。这是有文字记载石鼓书院诞生的准确时间,石鼓书院成为宋初四大书院中创建时间最早的书院。在吕温的扶持下,秀才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。只可惜,他在衡阳只待了一年半,就病逝于任上,年仅39岁。满怀仁爱之心的他恪尽职守、政绩颇著,老百姓尊其为“吕衡州”。后书院毁于唐末的战火中。
李宽的后人李士真,虽一举夺魁中了进士却不愿意入仕为官。997年,他找到当地的郡守,提出个人出资,在旧址上重建书院,以“石鼓”命名。他要承袭祖先遗志,要将书院建成读书做学问、开展学术交流的场所。中国古代书院从唐代开始萌芽,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。从皇帝到官吏,从朝廷到民间,都对培养人才、发展教育表现出深厚的兴趣与责任。
刘沆(995--1060年),曾任北宋宰相、集贤殿大学士。1035年,他来衡阳任知府,非常重视书院教育,于是奏请宋仁宗,请求颁赐院额。仁宗皇帝大笔一挥,又赐匾额又赐学田。此举意味着石鼓书院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。
时间的指针滑到了1185年,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官员和学者潘畤,作为中央派往地方的代表来到衡阳,他倡议对石鼓书院进行了重建。两年后,提刑宋若水拿过接力棒,继续拓展了石鼓书院的办学规模。竣工后,还请当时的儒学大师、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撰文记载此次的重修。朱熹在《石鼓书院记》中阐述了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,提出了“明道义正人心”的教育目的,不仅是对石鼓书院,更是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这篇《石鼓书院记》在2006年石鼓书院重修之际,被镌刻在石鼓广场那本石书上,象征其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和不朽的文化价值。

自由、开放与包容的圣地
仁宗赐匾、朱熹写记,石鼓书院在宋代众多书院中脱颖而出,响彻江南!
不同于官学的教条主义,石鼓书院一直有着开放、包容、自由的学术氛围,并且在宋明时期形成两次影响全国的学术发展高峰期。
南宋长期偏居江南,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郁结,一些人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儒学来提振人心、改变现状。当时,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湖湘学派的张栻、闽学派的朱熹、婺学派的吕祖谦,同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张栻出身高富帅,是当朝宰相之子,虽祖籍四川,但一直随父亲生活在湖南,后又赴南岳衡山拜胡宏为师。他曾多次到石鼓书院讲学,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宝和碑刻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为武侯祠所作的《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》。在这篇碑记中,他颂扬了诸葛亮的忠义精神,也借诸葛亮的事迹阐明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理学思想。石鼓书院成为张栻传播湖湘学派思想的阵地。也正是在张栻的影响下,四方学者接踵而至,石鼓书院成为了南宋理学传播重地和湖湘文化的发源地。
石鼓书院特有的学术氛围吸引了众多志士达人,他们像辛勤的采蜜人一般来到了这里。
湛若水,明朝一位与王阳明并驾齐驱的著名理学家,先后五次踏上这座书院,每一次的到来,都如同春风化雨,滋润着书院内求知的心灵。1556年,那是一个金秋时节,年已九旬的湛若水,不顾年事已高,再次来到石鼓书院,一呆就是60天。也许是最后一节课,当站在书院那熟悉的讲堂之上,他凝望着窗外,心中涌动无限的感慨,于是在讲堂的墙壁上挥毫题下了《石鼓书院讲堂题壁》。在这首诗中,湛若水仿佛与石鼓书院、与流淌的江水、与静默的石鼓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对话。他对石鼓书院的思念,超越了言语,化作了那永恒的笔墨,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邹守益,王阳明门下最得意的弟子之一,昔日以探花及第之姿荣耀入仕,官拜南京国子监祭酒,位尊而权重。然其性情刚正不阿,直言敢谏,终因触怒权贵,被罢官免职。于是,他毅然决然踏上归途,回到故乡,以讲学为业,矢志传承学术薪火。嘉靖中叶,邹守益受王阳明之托来到石鼓书院。他的到来,如同春风吹拂,为这片学林带来了勃勃生机。在讲坛上,他解答疑难,旁征博引,往往能结合身边琐事,辨析入微,深入浅出。他的语言,如同春风化雨,形象生动,听者无不心旷神怡,心悦诚服。邹守益更将这份对学术的挚爱,倾注在与石鼓学子的讨论之中。他将讨论的精髓,悉心整理成《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》,流传后世,成为学术瑰宝。这部作品,不仅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,更见证了他与石鼓书院的不解之缘。
甘泉学派的湛若水与阳明心学的邹守益,两位学术巨匠共聚石鼓,使得石鼓书院成为明朝学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站在合江亭上远眺,滔滔湘水奔流不息。石鼓书院以其广袤无垠的开放胸襟与深邃博大的包容气度,吸引着四方名儒、八方大咖。这里成为了一流学术大师的汇聚之地。他们如同群星璀璨,交相辉映在石鼓的苍穹下,共同织就了一幅绚烂多彩的学术画卷。
石鼓书院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,屹立于历史的风雨之中,博大精深,令人仰止。它不仅仅是一种追求真理、探索未知的执着,更是一种兼容并蓄、和而不同的智慧。这种精神成为了“石鼓著名穹壤”的坚实基石,让石鼓书院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成为了后世学者心中永远的圣地。
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缮,石鼓广场再度对外开放。近日,将儿子从电脑游戏中强行拽出,一家三口驱车来到了石鼓广场。
迎面而来的是一座三门四柱式石雕牌坊,高12.2米,宽19.8米,采用芝麻白花岗岩建造,上书“石鼓江山”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站在牌坊前仰望,泰山压顶的磅礴气势席卷而来,不由心生出敬畏之感。
这里,就是衡阳八景之一“石鼓江山”所在地。
这里的石鼓,曾经被人敲响
石鼓广场的北边就是石鼓山,石鼓山因曾有一面敲得响的“石鼓”而得名。
这并非传说!
郦道元,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,在他的《水经注》里有一段描述:“县有石鼓,高六尺,湘水所径,鼓鸣,则土有兵革之事。”罗含,东晋时期的杰出人物,出生于衡阳郡耒阳县,也是一名地理学家,曾写了一本《湘中记》,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、特产、民俗、古迹。他也证实,确有此事,并且“扣之,声闻数十里”。
每当石鼓发出鸣响时,当地就会有战争或动乱的事情发生。百姓觉得此事不祥,于是有一名叫庐龙的勇士,将石鼓推入了崖下深潭。这件事被记录在了《祥符州县图经》中。为感谢这位勇士,石鼓山上曾经建有庐龙庙,用以祭祀他。
1637年,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来了衡阳,先后两次登上石鼓山。喜欢探究的他想找到那个高六尺的石鼓,却只在合江亭下发现两根镌刻着对联的石柱。
在石鼓山附近的筷子洲上驻扎的湘军也派人潜入深潭寻找石鼓,却只在潭底发现一洞穴,阴森恐怖至极。此后,石鼓的下落,成为不解的谜团。
走进石鼓书院的山门,你可以看到大门右前方有一面石鼓,这是1965年修建石鼓公园时凿刻的,已是一面敲不响的石鼓。尽管如此,它仍然是衡阳人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。你、我,还有他,曾经在年少不更事时爬上那面石鼓,与它亲密合影留恋。今年提质改造后,石鼓广场在南门入口处新添了一面别具新风的石鼓。这面石鼓嵌有电子显示屏,能够展示声音和图像,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与听觉体验。

记者手记
“石鼓江山锦绣华”,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,我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恶补衡阳文史知识。感谢戴述秋、刘洁,他们俩对石鼓书院的执著钻研,为我的采写提供了捷径。我多次独自前往石鼓书院,在石鼓山四处寻觅,努力探究它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火。不管是李宽,还是张栻,亦或是湛若水、邹守益,他们所追求的,无外乎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,也是王船山一直所倡导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
>>我要举报